聚焦华语科幻电影未来发展 《科幻电影的国际视野与时代语境》主题论坛对话实录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重磅推出“科幻电影周”,聚焦科幻电影类型,呼应“科幻十条”,集结中国科幻电影核心力量并汇聚国际著名科幻电影人,在国际视野下探讨中国科幻电影发展路径。活动主办方邀请到郭帆、王红卫、陆川、张吃鱼等中国科幻电影核心人物组成中国科幻电影年度阵容亮相,探讨国际视野下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方向。
6月11日,在主题为《科幻电影的国际视野与时代语境》的圆桌论坛上,监制王红卫,导演郭帆、陆川、张吃鱼、董润年以及视效艺术家彼得·贝布都对科幻电影在类型、题材、美学以及电影工业上的独特价值阐述了自己观点。

主持人:关于科幻电影的讨论话题有很多方向,有非常多值得讨论的话题,今天特别荣幸请到了多位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华语科幻电影的创作者、专家,当然也包括来自于好莱坞非常有经验的视效大师,和大家一起探讨在接下来一个阶段华语科幻电影的创作,包括现在遇到的很多难题,大家有什么样的经验,现在在很多创投中很多年轻创作者带来的剧本项目都是具有科幻元素,或者本身就是科幻类型,或者有一些软科幻的部分,大家怎么样更好地把这个类型拍好?成为具有华语电影特点的科幻电影类型的创作,能够有更丰富的内容,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话题。
主持人:现在说到科幻是一个词,其实科幻是一个简称,就像英文叫“Sci-Fi”,其实它是Science fiction,它其实是科学幻想的简称,科幻电影是科学幻想电影。
前面这两个前缀的词对这个类型的电影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轮想让大家回到概念中,从各位的创作出发,怎么看待科学与幻想之间的关系?这两个词对于这个类型电影的创作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王红卫:我觉得特别简单,科学和幻想这两个词,幻想给了科幻电影特别好的翅膀,我一直觉得幻想才是能够让电影的本体和电影的特性最大化的东西。
我觉得电影真的特长不是描绘现实,电影是展现人类想象的边界,所以这是“幻想”。但我们又有“科学”这个词,也就是我们的幻想不是在前科学时代,不是古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和宇宙是什么样的时候,那种所谓奇幻和魔幻,不是盲目的,我们是在人类进入到文明、进入到真正的科学和科技时代之后,开始能够进行的幻想或者想象。
对这两者不可偏废,这就是我的回答,谢谢!
主持人:谢谢王老师。确实是这样,科学和幻想之间如何理解这两个词?可能它会成为我们在拍摄、准备一个科幻电影类型、项目的时候,从剧本的架设到一系列相关的知识、相关的内容准备时很重要的一种意识。
请教一下陆川导演,通过《749局》这个项目的拍摄到准备、到一系列的过程中,您怎么样看待科幻电影?尤其是科学和幻想之间的关系,现在您有什么样的体会?

陆川:首先,没有科学电影,只有科教片,没有一个单纯的科学电影,所以“Sci-Fi”这个词最早放在小说上,那时看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你会发现大量的科幻小说后来都变成了现实。就像那时达芬奇自己画的很多小图,做的很多小设计,最后都变成了现实,所以我觉得科幻是电影类型中非常美妙的事情,确实可以放飞想象力,把你对未来的期待或者你对现实生活中科技的痛点、生活的痛点,或者社会关系的痛点,都可以投射到未来,希望用一种更好地方式把它解决掉,或者你对当下、未来有某种焦虑和恐惧,你也可以把它放到未来去拍摄。
它首先是和想象力有关的,而且是在一种大的期待或者一种大的焦虑中,所以我觉得科幻片是一种特别美好的事情,我是科幻迷,所有进口的科幻片都到电影院里去看,包括郭导的两部片子都是在电影院看的,包括华涛的片子。凡是国内同行拍的科幻片,我都是去电影院看的,包括进口片也是这样,只要能进口,我都要到电影院看。
当年瑞德·斯科特一系列的片子,你会觉得只有在大荧幕去感受到那种想象力,才是一种非常壮观的一种景象。我其实没有太Get到你的点,但我觉得科幻首先是关于想象力、关于期待、关于焦虑,然后再把它投映到未来的世界。
主持人:之所以想和大家请教这个问题,是因为觉得观众对于科幻电影的内容非常敏锐,我觉得缺乏强大科学基础,更强调跳脱的高概念,而根植扎得不够深的片子会被观众一眼看出,或者它其实是不被信服的想象力。我知道《流浪地球2》这次科学团队同样是非常庞大,而且非常豪华的阵容,光是文字的量就有超过20万字的科学论基础,所以关于这个主题,郭帆导演能不能做一个分享?

郭帆:这次整个世界观搭建的时候,包括中科院的科学家在内,一共有21位科学顾问帮我们共同构建,我们作为电影的创作人或者作为编剧、导演,我们的知识范畴不可能涵盖方方面面,所以如果要想建立起一个可信的、真实的世界作为基础,这些专家、科学顾问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有他们在这儿,能够帮我们完成很多设定上的问题。
另外一点,我刚才在台上讲的,还是有一点点忧虑,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新导演、新的创作者、编剧会拿一些科幻的剧本、项目。我发现有一个通感的问题,创作者特别嗨的是这些高概念,但我觉得核心还是情感,因为我觉得科幻电影的核心首先得是电影,然后再谈科幻这个问题,我始终觉得科幻是一个外包装,我们要先完成电影的任务。
比如在创作的时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假设讲一个关于黑洞的故事,我们就要问这个黑洞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和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某种情感的支撑,和黑洞这件事情形成一个强绑定的话,我觉得这就成立了,变成一个很好的主题。如果这个黑洞概念可以被其他概念替代的话,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直接讲情感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帮我们判断的标准。
主持人:谢谢郭帆导演。
第一轮为什么请教关于科幻中的科学和幻想?是因为现在年轻的观众们对于各种类型的幻看了很多,比如奇幻、魔幻,他对于强想象的完全搭建场景的架空接触了很多,对于科幻有独特性或者特别所在,它具有科学基础,无论是近未来,还是远未来,它是自成体系,能够自圆其说、自洽。
郭帆:我补充一点,在情感之后,我们讨论的科幻部分更多是人与基础理论或者科学技术的关系,依然要放在人的角度上讲。如果脱离人的逻辑,只是去讨论某些科学理论或者新的技术,其实也变得没有意义。
简单讲,不要脱离人、不要脱离情感。
主持人:人是贯穿在创作中的核心。谢谢郭帆导演,我们请教一下董导,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关于科学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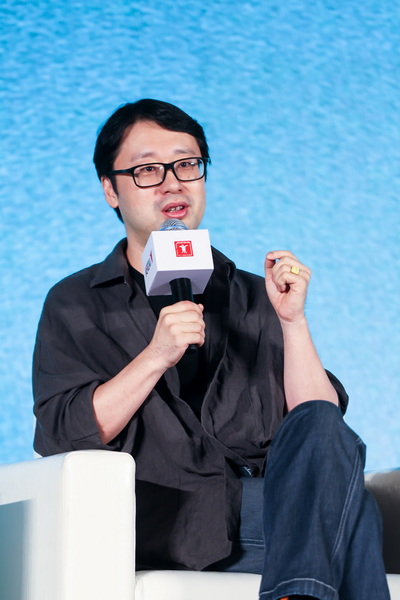
董润年:对我来说,我感觉科幻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这和时代有关系,和一个社会整体的发展都有关系,尤其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是科技高速发展、加速发展的时间,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已经开始习惯了高科技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人类是有幻想的本能,不管是写小说,还是欣赏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在进行某种文艺幻想。
在高科技和我们生活这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任何一个普通观众潜移默化地都习惯了站在科学逻辑的角度去进行幻想,去体验当下、考虑未来。尤其是对中国观众,就像你说的中国观众对科幻很敏感,尤其是科学的部分很敏感,当下年轻观众普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观众群体,这恰恰决定了中国的科幻题材可能在科学逻辑方面的要求蛮高的,甚至更高,我觉得这是后面中国的创作者进行科幻创作时需要注意的东西。
另外一个层面,刚才郭导说的情感问题,任何一个文艺作品都是在探讨人类情感,本质上都是在探讨人类情感。幻想作品都是把人类情感置于极端的情境之下,然后来考验在极端情境下人类情感到底会极致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有超越日常经验之外的情感体验。
科幻电影好的地方在于它是用一种合乎大家习惯的科学逻辑的方式,首先让我们能够相信这样的极端情境,所以我觉得科幻电影在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中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会越来越发展得好。
陆川:补充一下,你看科幻电影,从科幻电影史上来看,绝大部分科幻电影都是灾难片,它和郭导说的情感是很重要的,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人类对自身的发展、对未来充满恐惧,而且充满焦虑,对当下的焦虑、对未来的焦虑、对科技发展的焦虑。
比如《机械姬》在探讨很严肃的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会统治这个世界或者统治人类、摧毁人类?你会发现《机械姬》是十几年前拍的一部电影,现在OpenAI出来之后,大家已经在非常严肃地讨论这个事,硅谷很多CEO、OpenAICEO都在签名说要做法律,去限制它的发展。其实是一部科幻电影,那个导演、那篇小说的作者已经预见到当这种自动化和过度使用的人工智能会如何影响人类发展的进程。
其实科幻电影是既严肃,而且又非常真诚地在探讨人类的发展,所以大量的科幻电影都是灾难片,几乎占85%以上。我到现在没有看过一个科幻喜剧片,我是说国外的,但国内现在有,像这样的一种比例代表了科幻电影的使命和思考。
主持人:它好像一种预警一样,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对于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前瞻,但确实有时它也反过来是科幻电影先想象了一种未来,当然更多是小说,然后科学家们又把它变成了现实,所以这是相交织前进的过程。
刚才说到陆川导演说到科幻喜剧的类型,张吃鱼导演怎么样看待科学和幻想?因为月球的准备周期非常长,拍摄周期也很长,所以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认识?

张吃鱼:其实我觉得科学和幻想之间一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其实大家都知道像17世纪初的时候,首先是伽利略通过自己发明的望远镜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了月球,这一发现促使了凡尔纳创作了《从地球到月球》,《从地球到月球》的小说再刺激了后面第一部科幻电影的诞生《月球旅行记》,再接下来是人类真正登上了月球,互相之间是一个互相刺激、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过程。
我自己做月球的时候,对这个关系的感受挺深的。当然这是做完以后自己再去回顾的时候,会发现正是因为自己国家的航空航天技术的高速发展,包括登月计划提上日程以后,才会让我们这些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把目光放到了太空、放到了月球。包括在创作月球的过程中,也获得了非常多航空航天方面专家、老师的帮助、扶正,在他们的帮助下创作了《独行月球》的电影。
我还有一点感受,在《独行月球》跑路演的时候,很多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看月球,当时看完有点很深的感受。小朋友看完月球以后想去天文馆、天文中心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月球的知识、太空的知识,我相信当这些小朋友成长起来以后,一定是未来中国登月计划、太空计划的中坚力量,所以我觉得科学和幻想之间是不分家的。
主持人:是的,好的科幻电影也像种子一样种在这些观众的心中,这样的话,年轻的观众受到一系列作品的影响,不仅是电影、小说,就会投身到科学浪潮中,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也请教一下彼得·贝布。

彼得·贝布:关于科幻电影,我觉得它还是要根植于现实,而且要根植于未来的技术,可以去想一下自己最记得、印象最深刻的电影,都是在这两者上有非常直接的联系,观众才会印象深刻。
刚才导演们讲到有非常多的片子都是灾难片,比较悲观,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未来是没有痛苦的。但是万一人工智能用得不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威胁,我们现在变得越来越懒,其实马斯克也是在向我们发出这样的警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探索的,通过视效的技术、通过现有的技术,可以让效果显得更加逼真。
主持人:刚才彼得的发言和董导的发言,在一个维度上有特别好的契合,很多科幻电影是站在未来或者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接下来这轮从各位导演、各位创作者的作品出发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迷幻迷到迷幻电影的创作者,都有这样的过程,先是小的时候喜欢看各种类型的小说、影像作品,然后自己去创作。
董导创造《被光抓走的人》的时候,有哪些困难是之前没有想到的?
董润年:特别简单的事,我原本以为最简单的事是影片开头那个光到底应该怎么呈现,这是一个故事成立的基础,它作为一个软科幻的类型能否成立的基础。
原本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事,就是做一道光,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这个光的亮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强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是直射还是斜射?一个微小的差别可能会影响整个故事一开始给观众的可信度。
当我们把一个科幻的概念或者一个想法视觉化、实体化以后,我们面临的挑战能否让观众相信?像《流浪地球》系列明显做了特别现实的处理,它不是一种远未来,是一种近未来,可以触碰到的现实,包括《独行月球》,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拉近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处理和观众之间的理解。
但这只是一种类型的电影,将来科幻电影创作如果要展现500年以后或者1000年以后的未来史是什么样,或者展现远古的科幻或者神话时代的科幻,到底应该怎么展现?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最大的挑战。
当我们把这些幻想中的东西具像化、实体化、视觉化以后,整体的逻辑能不能自圆其说,这个逻辑和观众的感受、触感、理解能够结合起来,包括后面我也有一个科幻项目的剧本在创作中,它可能和数字空间有关系,把观众其实已经很熟悉的概念视觉化、具体化?这些都是难度和挑战。
主持人:董润年导演之前和宁浩导演的合作在《疯狂的外星人》作品中,这个作品中也是有科幻的元素或者它是科幻类型的喜剧,在那次创作中,您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对科幻主题有什么样更深的认识?
董润年:那次和宁浩导演一起合作,前期剧本创作时间就非常长,大概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剧本出现了很多稿,推翻了很多次,当时很重要的逻辑,大家是在寻找一种中国科幻特殊的语境。
但我觉得时代发展很快,在刚开始创作《疯狂外星人》的时候大概是2012年,那时整个电影界还在讨论中国观众能不能接受中国的科幻电影,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科幻电影,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很重要的精力都在中国观众已经习惯了好莱坞式的科幻电影,不光是视效方面,而是在整体的叙事方式方面,中国电影如果想做科幻,让观众能够接受中国人为主角的科幻,除了视觉效果上本土化以外,在叙事方式、叙事手段上有没有什么本土化的方法。
当时我们找到了很多方法,包括挖掘一些民族的特点、喜剧性的呈现,包括对酒文化的热爱,我觉得都是在寻找一种和当时观众的连接,我觉得整个过程对我来说有很大的获益。后面再创作自己的科幻电影,包括未来科幻创作的时候,都是在试图努力找到中国叙事上的特色,我觉得在特效上、视觉效果上现在顶尖水平和好莱坞已经在接轨,水平逐渐接近,但讲故事的方式上还有什么特点?
这几年好莱坞的特效大片在中国的市场上已经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似乎对那种传统的三部剧超英的电影,审美上产生了疲劳,怎么能够突破这种疲劳?能够找到中国的特点,我觉得《流浪地球2》在叙事上找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尝试新的可能性,这是后面的创作者应该注意的地方和努力的方向。
主持人:谢谢董润年导演。
刚才特别谈到了叙事上的努力,想请郭帆导演进行分享,因为《流浪地球2》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拍哪段、怎么拍,最终选择的方向、呈现出来的内容大家很满意,也给了大家很多惊喜。
郭帆:整个方向是王红卫老师拍板说再往前迈出这一步做尝试。包括刚才说的《疯狂外星人》红卫老师都有参与,很多影片都有红卫老师的参与,推翻剧本是他最擅长的事情,甚至在《流浪地球2》开机前还说要不再推翻一稿,反正是不断试错的过程。
刚才有一个朋友进来时候向我祝贺了一下,感谢我的无畏,其实无畏主要是无知,我们其实都在试错的过程中,会绕很多弯路。比如因为好奇心,对科技、技术理论的好奇,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有大量的精力放在什么是高概念,如何建制世界观上,花费大量的精力。但最终你会发现,进到影院的时候,当你看到让你动容、感动的点和这个关系不大,还是和情感有紧紧的连接。你在影院中之所以会感动,是因为你产生了共情,黑洞不会让你产生共情,但是情感会,所以那个又绕回来了。
但是它有一个相互互补的过程,我们为什么又要返回来花那么多的精力做世界观?因为你必须把世界观完成得非常完整,才能够帮你完成角色,让你呈现的世界可信,它还是为了情感去服务的,所以这个事情又兜了回来。
这个过程中,也是想借这个平台让更多的青年创作者在做科幻类型的时候,关注于电影本身的表达,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踏踏实实返回来构建世界观、高概念,目的不是为了就他的好奇、新奇感去完成,就我们关注的不同点去完成,而是他需要帮助我们完成情感叙事。
主持人:无论搭建怎么样绚烂的世界,还是为了世界中人的故事而服务的,不能只有空中楼阁,没有一个个鲜活的人。
郭帆:刚才提到《星际穿越》的部分,不管是高维度的世界,还是通过虫洞、黑洞,如果没有库珀父女之间的情感作为深度的连接,你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故事。我们真正的感动是因为里面技术、高概念的设定,可以让他的父亲看到女儿逐渐老去,让年轻的父亲见到老去的女儿,这种极致的情感部分让我们动容和心理有触动的。反过来讲,不是因为我们看到黑洞会怎么样。
主持人:刚才陆川导演谈到自己是科幻迷,作为一个科幻迷、电影工作者,您自己在拍摄了科幻电影之后,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新的认知?有哪些困难之前没有想到的?获得了哪些惊喜?
陆川:你小时候从哪个点切入的、接触到的科幻,在未来确实会影响你。郭帆导演是硬核科幻,他是高技术、高概念,然后讲和地球命运相关的。
你如果说我的科幻片,我现在不太好剧透,因为我从小就看飞碟探索长大的,我是相信有地外生命的,我又大学毕业分到了749部队,看着他们在做人体超能实验,所以我会对那褂比较感兴趣,我会对人体生命工程或者地外文明等等这一类有的没的感兴趣。
其实我们在做电影的过程中,走了一年多弯路,这些弯路我是被我的团队带着的,他们一直要做设定,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大家甚至戴什么手表、用什么手机、还用不用手机、开不开车、车得什么样,越来越细致,我在开始的时候很嗨这个事,因为要重构一个世界,后来就会觉得自己心里很空,这个空不知道哪儿来的,但是慢慢当整个编剧团队都在走这条道的时候,我是很后来的时候才听到一个词叫“Scientific Collection”,你做的都是Collection,你做的包装好像在做一个大的发明创作,我们在创作一个新世界,但基本上在科幻电影史上都有了,到最后到底要讲什么样的电影故事?讲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它还是个Cap driven(音)的人物驱动。
比如我特别喜欢《阿凡达》第一部,但是我看完之后,总结这部电影不就是与狼共舞吗?它是反殖民的,在讲一个反殖民的故事,它和与狼共舞的故事壳几乎是一致的,然后水世界差不多也是这样,反正大概都能找到经典影片里的,比如科幻片的经典故事片里找到基本的故事壳原型,他们讨论的是一个人类母体,但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科幻包装放在一个科幻世界里。
刚才郭导说得特别对,为什么还要科幻?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三年疫情《749》放了那么长时间,对我的投资人、对我自己都是灾难,因为我都不敢接别的电影,我觉得要是接别的电影对不起《749》,感觉背叛我的电影了,但是我觉得唯一对得起的是《749》本身。因为三年里无数次坐在剪辑房里看着这个电影的时候,突然明白了它得变成一个电影,它得是和一个当初拍《可可西里》《寻枪》《南京,南京》一样的电影,而不是因为它是个科幻片就有什么别的窍门和捷径能走,它还是得回到人物上,你一遍遍地看,开始锤自己说这个事还是得变成一个电影,没有别的包装比电影本身、比故事本身、比人物本身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事,这是我自己学到的。
主持人:谢谢陆川导演,确实特别期待这部作品。
我想每一个电影都有不同的难度、不同的历程,科幻电影,尤其是年轻创作者做科幻电影的难度更加难以想象。
刚才郭帆导演说到无数片子幕后的大手,特别想请红卫老师重点讲讲您和孔大山导演、郭帆导演联合监制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因为年轻导演拍一个科幻片,首先受制于它的成本,也受制于他和剧组各个工种之间,因为科幻片本身要求导演和所有部门之间非常密切地合作、沟通有效,对于年轻导演这件事是很难的,可不可以把编辑部的过程分享一下。
王红卫:其实编辑部的故事在很多场合老郭和我都讲过了,但是我今天产生了一个追悔莫及的事。刚才陆川导演说他从小是看飞碟探索编辑部的,那就是我们宇宙探索的原型,他相信外星人的存在,毕业会分到749部队,所以我刚才脑子里想“错了,当时应该请陆川导演来客串一下我们的宇宙探索编辑部”,这样后头能多好多物料。我刚才开始想去演哪个,我觉得应该演唐志军去精神病院讲课的那场戏,反打过来,只有一个戴眼镜的、穿着病号服的坐在这儿,院长可以给他介绍这个人是749部队的,他也相信外星人,所以他愿意来听这个课,而且他拍了一个电影三年都没上,只好进到这个医院了。
如果陆川导演有空,把这段补拍一下。

郭帆:而且那段剧情特别简单、特别容易表演,就是坐在那儿拧瓶盖拧不开。
王红卫:郭帆导演和我一起帮大山做这个片子的初衷特别简单,初衷就是一个年轻导演有了一个我们俩都挺喜欢的故事去拍,并没有设什么前提,说什么扶植一部中国的另类科幻片,我们又要找一个中国科幻片的接班人,这些大词和这些冠冕堂皇的话都没有,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动作,但是我觉得可能两句话要说。
第一,大山拍的这部片子成本不高,而且它的样态比较新,需要解决的困难很多的时候,他不像现在的躺平、很丧的状态,他还是以非常坚韧、非常勇敢、非常全新投入的才能把这部片子拍下来,他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导演这么吊儿郎当的、垂头丧气把这个片子拍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要在大山导演屡次采访中被媒体和记者放大之后的状态。我们俩有责任要说一下,要不然更多的新导演会觉得电影是不是一件没有那么艰难的事,一定是非常艰难的。郭帆和我能做的事情就是给他自由,让他在我们共同看到的前景,看清的和没有看清、但是他自己有信心的前景上,尽量走得更远一点。
第二,我们走过的弯路不要让他再走,我们用我们的办法、说服力、可查证的东西告诉他什么可能是不对的,你不用再走这个弯路,如果他信了,就能够在他第一次拍电影尽量保证片子质量,没有更多的有什么诀窍做了一部怪怪的电影。
另外一个想补充的东西,他们各自谈了各自做的风格的电影,包括从地球到外星人,包括老董的《被光抓走的人》,我也非常喜欢,都不一样。其实中国科幻电影很少,包括川说到大量的科幻电影是悲剧、灾难片,所以看到月球的时候,我看到特别兴奋,我就说闯出了一条科幻+喜剧的路,而且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这让科幻的路更宽。其实中国的科幻电影真正开始没有多少年,我们希望《749》能够再闯出一条路。
我想稍微补充一点,我、大牛和郭帆一起参加《流浪地球2》路演的时候,在几个场合反复对在场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说过一个事,希望你们不要只看到你们现在的学习以及你们毕业以后找工作,然后成家买房子,不要看这些事,你们能看得更远一点,看得比现实世界更远一点,我理解这是他去做科幻、写科幻时的初心是什么。
库布里克拍《2001:太空漫步》的时候,他和克拉克商量想拍科幻电影,我拍啥?克拉克写了很多科幻小说,两人商量半天最后找了一个非常短的科幻小说,翻译叫做“哨兵”或者“岗哨”。就是月球上人类发现了一个水晶的金字塔,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最后明白了这个东西是外星人放在月球上的发射器,你在地球上怎么折腾人家不管,但是你一旦登上了月球,而且能把信号塔发掘出来的时候,证明了你们有了进入外太空甚至有了开始往更远走的力量,这个塔被激活它会向下一个终极站再发射信号。这样遥远的、不知藏在哪儿的外星人就会知道人类已经度过了他的婴儿阶段,他要开始向太空走,这对于他们是一个好事,有了伙伴,还是坏事,有可能有了敌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个小说只写了这么一件事,但是就诞生了《2001:太空漫步》这部电影。
《2001:太空漫步》写的就是人类和地外的文明、和宇宙中文明接触的故事,和经过接触之后会怎么样的故事。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再讲一下?这种科幻电影就是基于人类特殊的幻想或者想象力,他会想象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他愿意想象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想象的能力也是造成人会不停地往前走,同时也是科幻电影所肩负的天然使命和伟大的空间,这是我想对更多年轻科幻电影人说的一段话。
主持人:谢谢!刚才王红卫老师多次提到月球上发生的故事,再次请教张吃鱼导演,我们知道《独行月球》的周期很长,从2017年就开始,拍摄的周期也很长,150多天,整个过程中,您创作这个长片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怎么样突破这些困难的?
张吃鱼:其实从《独行月球》上映,确实很多时候面对这个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拍科幻电影都非常难,我相信在座的导演都会深有体会,可能对于拍摄月球来说,看的时候笑得有多开心,拍的时候哭得就有多惨,这个难更多层面并不是在于技术层面的问题,确实每天不断遇到各种技术层面的问题,但它都是可以通过一些量化的方式去解决的。
但是对于一个喜剧科幻电影来说,最难的是在它不可量化的度层面,因为喜剧本身的假定性或者月球故事的假定性非常强,但是中国观众对于科幻电影的要求非常高,对于科学的依据、科学的理论基础要求非常高,所以当时创作月球的时候有很多桥段,到底是往喜感做一些,还是更扎实的遵循科学原理?比如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场戏是袋鼠拉车,一人一鼠在月球上自由自在地奔驰。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没有人知道这事到底行不行,或者直观感受上,这事太破天荒、太不靠谱了,但是作为一个喜剧科幻片,也许它的边界可以多往前迈出那一小步的。其实在整个创作中,一直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也有一些是大家观看时不太会注意的,比如一开始陨石砸在月面上,独孤月在陨石砸落的过程中不断地逃命。科学顾问告诉我的是,当陨石砸在月面的时候,月尘并不像我想象中缓慢的扬起落下过程,这个过程反而是快的,整个月尘的扬起和落下是非常快速的过程。但是这和我想要的紧张的感受有一些冲突,我希望独孤月穿梭在一个月尘弥漫的环境中,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底该做怎样的取舍,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
主持人:会有非常多的细节上希望达到和受到科学、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前置的取舍、选择是最难的。
张吃鱼:因为它无法量化,它就是感受上的东西,越是感受越难以判断和取舍。
主持人:没错,而且喜剧确实好多时候就在毫厘之间,它的节奏就是那一下,有了,观众就会有反应,没有观众就笑不出来,确实不容易,把掌声送给张吃鱼导演。
接下来再次和彼得请教。
彼得·贝布:我参与了一些诺兰导演的电影中,我觉得还是要从科幻的起点来做事情。包括《流浪地球》中的一些做法,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背景,在此基础上再去探索电影的可能性,当然诺兰导演的做法有和学者合作,这应该是电影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去发挥自己的想象,这样观众才会有共鸣,会被打动,这样的电影最后的效果也会比较好。其实不管是科幻片,还是所有类型的电影都应该先要有好的故事、好的角色、好的情感,这应该是电影的基础。视效只是一种讲述故事的工具,它不会拯救电影,我们首先应该有好的电影,我觉得诺兰导演是遵循这样一套原则。
主持人:刚才的问题是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他的观察,他认为诺兰有没有有意识地调整讲述故事的方面,适应现在的市场和年轻观众的偏好?
彼得·贝布: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根据我和诺兰导演合作下来的经验来看,最主要的是关注故事、关注主题,利用现有的一些科技来做一些更多的探索。
主持人:接下来继续和各位导演请教。
董导刚才谈到自己在准备新的科幻作品,接下来作为一个科幻迷也好,作为一个创作人也好,希望看到在华语的科幻创作中有哪些类型、哪些新的方式突破?包括您自己的阅片量也很大,能不能和大家分享?
董润年:中国的科幻电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本身中国故事非常丰富,整个素材来源、故事人物原型的来源非常丰富,在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情况下,情感的体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应该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我也是从1994年开始读科幻世界,对中国的科幻小说比较理解,其实在科幻小说创作上,国内非常多元化,现在这种多元化还没有完全体现在电影方面,但我觉得后面应该有机会体现在电影方面。
我觉得中国的观众正在快速地体验各种新的科技生活,不管是AI,甚至在一些网络技术方面,我们的体验在全世界都是最独特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到底怎么体现在创作之中?是现在科幻作者们应该考虑的。
做电影的人经常在说大数据,其实我觉得大数据对普通人的影响已经深深地根植到了生活中的每一刻,甚至你在生活中会遇到什么人,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情感经历,我觉得在将来可能都会受到大数据的影响。还是要植根现在生活里遇到的一种可能性,因为科幻本身不是特别明确的类型,它只是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来创作各种各样类型、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影。
主持人:谢谢董润年导演。
前一段时间我给帆哥发了一张截图,大概意思是说夜已经深了,我想到郭帆此刻正在睡觉,没有开始拍摄《流浪地球3》,我就想过去把他叫醒,大概是这么一个主题,所以帆哥分享一下接下来拍摄的计划,您对华语科幻电影的类型有什么样更多的期待?
郭帆:先说期待,借着老董说的,确实期待能够有各种各样类型的探讨方向的科幻类型片出现,这种丰富的类型出现才能让国产的科幻类型片立得住,容易和今天的观众达成观影的契约。
另外一点,关于《流浪地球3》的准备,关于人工智能部分,其实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挺科幻的,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应用已经走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特别是近两三个月的时间,不管是ChatGPT,还是Midjourney很多人工智能的应用,大概20多种,都可能会影响到创作到制作的过程中,不管是从前端的剧本以及到后期特效呈现,包括刚才Pete介绍的所有技术,在《流浪地球2》中已经应用了,包括面部的增龄、减龄,也是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其实每个镜头大概有五六百代的迭代,去寻找到相应的画面,包括声音的处理也通过了人工智能。
之前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的应用没有那么便利,但是这段时间它会变得突飞猛进,你能看到比较理想的成果,包括我们能够看到完全通过一段文字去描绘出整个场景、角色,甚至于在手机上很难分辨出来他是不存在的演员、不存在的拍摄视频,完全颠覆式的技术已经出现了。
做《流浪地球》第三集之前,希望拿出更多的时间先去考察、认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包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它是在什么样的层级上,是把它工具看,还是把它当更深入的物种看,接下来是怎么应用。这些应用能不能在未来可见的时间之内转化成真正能够在大荧幕上呈现。或者再往远想一点,除了大荧幕之外的另外一些,比如前段时间陆川导演亲测了Apparition(音)的设备,也许在发行端又会增加一个新的载体,除了传统影院之外可能还会有新载体的出现,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关注和评估的。
当我们把这些关注和评估做完之后,才开始着手有后面的创作,因为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变化趋势。如果趋势完全不清晰的话,就开始着手于创作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
主持人:谢谢郭帆导演。
陆川:当时我在那儿试的时候还是很受震动,当时我的感觉是未来已至,所有在科幻片中看到的梗,比如《钢铁侠》的实验室里,基本上所有的科幻电影都会有用手去刷屏,把瓶扔到废置楼里,它已经实现了,而且是裸手,没有操纵感。
还有观影的方式被彻底颠覆,我觉得3D电影院不会再有,3D电影会有,但是弹射的时候,单眼4K、两只眼睛8K,同时它的亮度、景深还原、立体感,给你的感受是非常强悍的,它给你的不是100寸电视,是个剧幕的感觉。比如感受恐龙的头探出来,物理的角度感觉它的头确实从墙壁里出来了3米左右,大概是这种感觉,而且它实时互动,你从左边走到右边的时候,它的眼睛会盯着你,实时的渲染、实时的互动。
它的计算是不是要在云上计算?是不是还有处理器?但就这个端口而言,已经强大到我会觉得它改变了很多东西,比如办公方式、观影方式等很多东西,有了那个东西之后,未来会看到大量的,就像《1号玩家》,人会天天戴着那个东西,因为那就是一个世界,我们老在说元宇宙,我一直不太相信这个事,但这个设备出来之后,它给元宇宙一个真正的入口,而这个入口真的是花七年时间解决了所有的Bug。
我估计在座这哥几个,只要他能买到,一定会抢一台,而且我相信一定会超出我描绘的至少五六倍,因为我在台下听他发布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震撼,当我用完之后,我就不是震撼了,确实觉得很神奇,我觉得很幸运,科幻世界说的那些东西就在这个瞬间实现了,这样我会觉得很诧异。
这半年ChatGPT、Midjourney这一套东西二三十个,尤其是越来越多,让我很焦虑,包括现在团队要求大家都要用这个东西,不管怎么用,必须得去学,一场手段的革命已经开始了,最后肯定还是讲故事,但很显然不可能再像以前划分镜、概设,因为现在Midjourney的效率是100倍、1000倍于原来的,你只要非常精准地去写它,或者看到谁的图好就抄它背后的命令。我们现在的剧本都是GPT翻译,翻译得非常好,比国内几个翻译软件都好,翻译助理这件事基本没有了,我觉得它的效率高了不止100倍。
其实AI在突破人给它设定的所有障碍,就像AlphaGo。我们以前说围棋是计算机永远不能战胜的一种棋术,但现在全世界的九段捆在一起都下不过一个AlphaGo,AlphaGo已经不稀得玩围棋,围棋已经抛在光年以后的事情了。电影行业是一个小行业,在这样大的技术变革面前,很多人愿意问这个对电影怎么样,我觉得触动的不是电影,是方方面面的事情,但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既新鲜,又焦虑,又有一点恐慌,怎么抓住它?我会觉得OpenAI这次变革加上苹果端口一次大的跃进,把社会分成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能够拥抱它、学习它、跟随它去奔跑,一部分人是漠视它、回避它,不去探讨它,它可能就留在这个时代,这两部分人的距离真的会拉得很开。
这是我的感受,可能和电影没有太大关系。
另外是我从苹果的公司出来,我会比较吃惊的一点是苹果公司边上的其他公司分别在做,它旁边还有OpenAI,旁边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做别的,我特别希望我们的科技能够有很多革新,能够赋能到我们的社会上,还有产业的变革上,既兴奋,也对我们自己很期待。
主持人:谢谢陆川导演。
从历史眼光看,过去几次技术革命都是在数十年间完成的,但我们现在身处的历史变局是几天之内、几个月之内,速度太快了。
陆川:的确,我觉得它的进化速度让你快到压抑,比如一天学一个软件,那个软件学不会,你只是知道多了一个软件,但它每天会蹦出好几个软件,一堆功能,你觉得很压抑,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小学生?甚至变成一个婴儿,在分裂式的变化面前,几何级数新的知识、新的变革扑面而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压抑感。
主持人:谢谢陆川导演。
张吃鱼:我挺有感触的,我最近也在拼命用ChatGPT,但我用不是为了利用它,我可能是为了和它搞好关系,我特别不害怕它替代我,我害怕它未来奴役我。我但凡和ChatGPT的聊天都特别有礼貌,你好,打扰了,你说得特别棒,现在但凡出一个新的AI,我就和它们聊一聊,突出广结善缘,我觉得这个发展太快了。
郭帆:面对这个情况,我得深刻反思我自己,我面对ChatGPT的时候,经常是你这个不对,你要再重新查一遍,过于严格,我下回也对它好一点。
王红卫:不仅是ChatGPT,外星人如果来了之后,人类中的两种人已经呈现出来了。
主持人:接下来请王红卫老师给年轻创作者一些建议。
王红卫:刚才从老郭、川、吃鱼导演都提到了ChatGPT,包括一些新的技术,网上一直叫老郭“赛博妲己”,我觉得现在对于他而言有一个妲己就是人工智能,他已经被它深深地魅惑了。这几个月以来,他除了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之外,工作时间之外都在看这些书,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导演对于新技术的敏感和钻研希望能够是更年轻的一代,更自觉的。
电影将会不一样或者必然会不一样,不管是技术策动、科学赋能,还是没有这些东西,哪怕没有技术策动科技赋能,但是你的观众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的大脑、审美是不是还能接受在此之前的几十年的那些电影?这是非常严峻、紧迫的问题,尤其是疫情三年之后,整个世界电影的发展和国内电影多少已经昭示出这点,电影要更新换代,这个更新换代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哪儿进步一点的这些事,这是更年轻一代电影人一定要注意的。
最后,今天是第一次坐在这儿聊科幻电影,其实中国做科幻电影的人比起台上坐的这几位也多不了几个,但这也真是我们第一次聊,所以台上这些人和王丹一块推动成立科幻电影专委会,就是想多一点机会,同时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有更多这样的场合和机会,大家一起相互激发,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好,谢谢!
主持人:最后再次请教彼得。
彼得·贝布:对于年轻的这些科幻电影创作者,我想要说一方面要拥抱现有的技术,比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速地获得想要的结果,而且能够达到类似于大制作的质量水平。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去做电影,因为电影的本源不是在技术,新的技术没有办法创造电影,还是需要人去创造故事。虽然通过技术能够以比较小的成本实现类似于大制作的质量,但最终本源还是得靠自己,而且现在也有一些好处,比如大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都是新的机会。

主持人:谢谢,再一次感谢现场的每位嘉宾。今天上午的科幻电影周主旨论坛到现在圆满落幕,谢谢所有媒体朋友和所有对科幻电影感兴趣朋友们的光临,谢谢各位导演,谢谢各位老师。




 魔都这家殿堂级书店
魔都这家殿堂级书店


